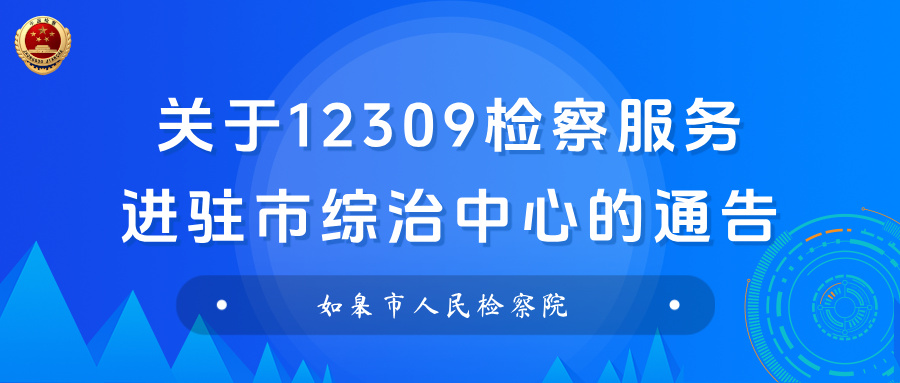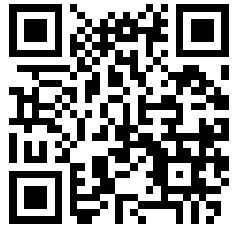在京城闯荡二十多年的我,时至今日,与朋友闲聊时会冷不丁脱口而出:“哎哎哎,我是个老农民哎!”语气中带着几分自得。在朋友半信半疑的眼神下,我通常会再提高声调补上一句:“这是真的,当年我插秧种田的水平可高啦!”
这还真不是吹的。那个“当年”,是指我到京城读研前的那十多年时间。那时我的父母正当壮年,才四十多岁,几乎每天从天亮马不停蹄地忙到天黑,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1.上小学读初中时,村里实行的还是集体劳动的生产队制,小孩子是没有资格赚工分的,自然不必跟着大人去田里地里干农活。工分是生产队分粮食的唯一依据,男性全劳力一天记10分,女性一天记6分。为多赚工分,父母申请为生产队养牛,一头牛一天加4分。我曾养过一头大水牛和一头小母牛。放学后,我的唯一任务是牵牛,年龄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则负责割牛草。
1981年,以种水稻为主的家乡小溪边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激发出村民们无限的劳动热情和高昂的积极性,他们一个个铆足了劲儿使出浑身解数来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当时,我家有六口人,分到的田有三大丘、两小丘,共3亩8分。哥哥和弟弟的田包括了子孙田,面积比较大,都有一亩多;姐姐和我各一小丘,还不到半亩,剩下的两丘分给父母。这些田,都不是什么好田。多年后,有一次与妈妈聊天,她感慨地说:“好多时候,眼前的吃亏不一定就真的亏。现在,我们的两丘田靠近村边,可以当宅基地建房子,就成宝贝啦。”这是后话。
那时,一年种两季水稻:早稻与晚稻,外加一季草籽越冬养田。爸爸既勤快又善于学习思考,采用科学方法种田。经过数年的栽种养田,这些田渐渐变成了土壤肥沃的好田,他种的水稻向来都是全村长得最好的,人见人夸!过了几年,我上了大学,户口迁走后要多交余粮,好在爸爸种的稻谷收成好,仅溪滩那一小丘的一季早稻就够全家交余粮了。
刚开始单干那几年,哥哥都在京城做木匠,长年住在大兴。每年春节前一周左右回家过年,元宵节过后出门。每次出门前,都有不少人家到我家商量,希望哥哥能带着他们的儿子做徒弟。哥哥是家里的荣耀,但家里的农活,他一直干得不多;弟弟才十来岁,正是一日三餐吃饭找不到人的贪玩年纪,也指望不上。因而,每年的“双抢”,一开始就只有姐姐和我帮父母的忙。全家人月光下种田割稻的场景,是我记忆中最为温馨的画面……
每当早稻成熟,放眼田野,金灿灿一片,沉甸甸的稻穗深深地低头藏在青黄相间的稻叶下。梯田式的田野,一丘高过一丘,大小不一。路边的水沟里日夜奔流着从水库里放出来的清水,临近水沟的稻田,每丘都有一个缺口可以进水。与马路平行的宽阔田墈是干农活时可以赤脚行走的主干道,自然比上丘与下丘之间的田墈要宽,也更结实。通常情况下,沿主干道生长的青草也更嫰更密,那是让牛走在水沟里两边吃草的好地方。水从高丘流向低丘,而放水是否方便是稻田好差的一个重要标志。
每年放暑假时,我都会算好时间回老家帮着父母干农活。在所有的农活中,对小溪边的农民来说,我一直认为最苦最累的就是夏季时的“双抢”。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即收割早稻种下晚稻,必须在半个月内完成,通常时间为7月下旬到8月初立秋前,这也是一年中艳阳高照、酷暑难耐的日子。要是家里的田多,干活的人手少,那绝对是一场披星戴月的苦战。
我家妈妈呢,凡事追求完美,总希望早稻多留几天让每一颗稻穗长得饱满,出米率高,这样一来,我家“双抢”的时间就更短更紧迫。那些年,家中的哥哥常年在外帮不上忙,弟弟又小,主要的帮手就是姐姐和我。关键是那段时间每家每户都忙得热火朝天,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帮忙。若是晚稻在立秋后种下,很有可能在没成熟时就遭遇霜降,导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农民靠天吃饭,对一年二十四节气特别在意。时令就是农民的律法,一旦违反了,老天爷会让你承担严重后果。
2.1985年的夏季“双抢”,是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次。那一年,已出嫁的姐姐随姐夫包工程去了,家中少了一个得力帮手。我呢,在县城上了三年省重点高中,刚考完大学回家。无论走到哪儿,邻居们遇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回家啦,现在毕业了吗?”接着又问:“大学考上了吗?”有的更直截了当:“美君,你大学考上啦!”事实上,刚考完试回来还不知道成绩的我,到底能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心里也没底,通常是含含糊糊地应付两句。从小到大,村民都知道我读书好,不管最后能上什么样的大学,在他们眼中都是天大的喜事儿。那时,全村还只出过一位大学生——他叫庞正忠,当年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现为京城著名的知识产权律师。
那年暑假,我一边在家忐忑不安地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同时为家中的农活出谋划策,成为父母的最主要帮手。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我拔秧种田的技艺进步飞速。
每年“双抢”开始前,父母都会根据各丘稻子成熟的先后顺序作一番统筹安排。晚稻不像早稻只有一个品种,而要分杂交水稻、粳稻、糯稻等,不同品种的生长期也略有不同。我心里有一丝担忧:一亩多的田,就爸妈和我三人,妈妈通常还要负责翻晒稻谷兼做饭,一天能割完吗?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清晨5点半,我们就踩着晨曦出发开工了。割稻速度要想快,就要姿势做到位。爸爸说:两脚尽量平衡分开,身子前倾弯腰半蹲,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稻秆恰好是一大把,身体重心随着要割的稻子在两脚之间作相应的移动,顺势转身将稻子码在身后,转身够不着时,就换放另一堆,每一堆都必须排列整齐,这样打稻时拿起来不会散架,打稻机也可直线前移而不必在水田里东弯西拐。我刚割一会儿就浑身汗水湿透、腰酸背疼,若不是看着爸妈年复一年都这么干活,我早就当逃兵了。
出乎意料的是,8点左右回家吃早饭前,我们就将稻子全部割倒码好了。早饭后,爸爸负责将打稻机打下的稻谷一担担挑回操场,由妈妈负责翻晒,妈妈还要做午饭和晚饭,外加下午点心。在挑走稻谷前,爸爸和我先将打稻机拉到一大堆码好的稻谷边上,这样,我一个人时仍可以继续打稻。说起来,干农活基本上是靠力气,但也需要动动脑子加上一定的技巧。割稻如此,打稻也不例外。割稻讲究姿势,打稻重在方式。双手紧捧一把稻子,用尽全身力气踩动打稻机,待转盘转得飞快时,先放垂下的稻头,慢慢地循序渐进到稻头根,再翻两下拉回稻头,一把稻谷就打得干干净净,同时又节省力气。中途来了表妹君明帮忙,大家鼓足劲儿,在晚上八点半天黑前总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务。算一算,从早到晚,一天要劳作15个小时左右。
说起来,每年“双抢”时,全家最发愁的是奓姆岙十七箩那爿地,田偏路远,将稻谷从田里挑到马路上,需走上一里多的田墈,再用手拉车拉回操场翻晒。要是一天割不完,天黑前,还得扛着打稻机这一重物,想想都费劲,非得请力气大的村民帮忙不可。为了省些力气,还要跟住在高爿地的那户人家说好话,将打稻机寄存在他们家走廊上一个晚上。
7月30日下午,爸爸把弟弟也叫上了。为了给枯燥的割稻来点趣味,爸妈、弟弟和我四人之间互相比赛,还给弟弟划出一小块,说那是台湾岛,割完了,台湾也就解放了,他就可以去玩了。就这样,你追我赶,结果竟然提早完成了。
如果一切都能按事先计划的进度割稻种田,在立秋前种完所有的田当然不成问题。但天天白天黑夜连轴转,干了几天,每个人都越来越疲累,越往后速度就越慢,尤其是像我这样平时很少干体力活的人,早就浑身酸痛、眼冒金星了。要是天黑了还在水田里干活,蚊子就像轰炸机,围着你嗡嗡嗡地叫个不停,咬得你浑身起包,又痒又恼。
那天下午,打完稻回家,夜色中我手拿镰刀爬上山坡上的小路时,一不小心竟然踩到了一条蛇,左脚第二个脚趾头被蛇咬了一口。我惊呼一声“啊唷”,走在身后的父亲急忙问:“没事吧?没事吧?”他手足无措,只是叫我快点赶回家,幸好我还能自己走路,脚趾头好像也没有马上红肿起来。回到家,隔壁的阿姆过来一看,说:“应该是无毒的水蛇咬的,不是毒蛇,要不脚早就肿得像馒头了。”阿姆的小女儿比我大两岁,前一年晒稻草时曾被毒蛇咬过,整只脚很快全肿起来如蓬松的馒头,不能下地走路,后用土草药敷了好几个月才好。
小溪边的俗话说:被水蛇咬的人会有好运气。我就指望着哪天会有好运降临。果不其然,第三天就有同学来通知我,我已如愿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通常,头天割完稻,将稻秆一把把捆好排在田墈上,第二天上午整理好水田,下午就开始插秧,天黑前,金灿灿的水稻转眼间就变成了绿油油的秧苗。
家里缺人手,一亩多的稻田,从割稻到插完秧,通常需要三天时间。父亲讲究种田时的品相,高标准严要求。他认为,一丘田要有田的样子才能插秧,比如:稻田的泥土必须全部翻新、松动、耙平,田壁整洁不留任何杂草,田墈削得清光漂亮。因而,头天上午爸爸赶牛翻土耙平时,我就拿镰刀清理杂草;中午,父亲再抓紧时间削完田墈。吃完午饭,父亲喜欢去家东边关公庙的石板地上躺一会儿,石板地凉凉的,午休特惬意。下午三点左右,太阳开始西斜,田水不烫脚时开始种田——要不然,嫩绿的秧苗会被烫死。
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的父亲,种田就更讲究了,他要求插的四棵秧苗成正方眼,横竖都是笔直的。一般人都认为只要竖行是直的,横的弯来弯去都在田里弯,有什么关系呢,还不一样割稻?但父亲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标准。他还要求每棵秧苗之间的距离在三十公分左右,说这样日照充足,稻谷才会饱满,不烂脚。这或许是他种的水稻总是全村最好最大的关键原因。
就这样,十多天中,全家人鼓足干劲,起早摸黑,总算基本忙完六丘田割稻种田的活儿。因人手太少,我们成了全村最后一户种完田的,这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成了常态。好在父亲精心管理的秧苗抽芽多、品质好,转移到大田后,没过几天,就日长夜奓,很快就追上了那些人家早种几天的水稻。收割晚稻时,那稻穗无疑又是全村最大的,人见人夸。
3.小麦,也是小溪边的主要农作物之一。秋末,那一爿爿溪滩地,重新翻整后,再一行行洒下小麦种子。一到冬天,溪滩上一整片全是绿油油的小麦。当时我家门前全是各家各户的菜园子,没建什么房屋,站在二楼廊下,可以远眺溪滩地,一望无际的小麦地,静静地耐心地等着春归。
在杭城读书时,听说城里人分不清小麦与韭菜,我甚感惊讶:它俩长得太不像了;但转而想想,小麦刚长出、离地面才20厘米高时,远看倒真有点像韭菜。只是在小溪边,小麦会大面积种植,而韭菜一般只在墙角旮旯种上一点而已。至今仍让我迷糊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越冬后的小麦,在开春前,有些人家会用脚踩小麦,说越踩分叉长出越多越稠密,收成越好。难道这是单子叶植物的特点?远离稼穑,我没有想着去细细考究一番。
小麦成熟是在每年的四月份,这时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缺粮食的,最难熬的日子就开始了,前后有半个月左右。记忆中,那段日子,妈妈时常会将牛栏间谷仓里的稻谷偷偷地送一些给姑姑,我们看到了也不会告诉爸爸,免得他心里不舒服。爸爸对姑姑是没得说的,要是他偶尔与妈妈吵嘴了,妈妈生气不做饭,他就会请姑姑来给我们做饭,但他认为姑姑家里缺粮,是姑姑的丈夫不勤快导致的。其实,那时缺粮食的人家比比皆是。过了这段日子,姑姑家种的番薯、川豆、冬瓜、豇豆什么的长成了,她总是挑最好的,送给妈妈。后来,姑姑的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成家立业,条件好起来不愁吃不愁穿,但姑妈的这一习惯多年未改。每次我回小溪边,妈妈拿出红薯、芋头煮时,会顺口说“这是姑姑送的”。
妈妈凡事追求完美,她总认为田芯村的师傅磨的小麦粉白一些。机器磨的小麦粉,一般分白粉和二子粉,白粉用来擀面皮、包扁食、做包子,而黑乎乎的二子粉只能做面条。为了多出点白粉,妈妈总让哥哥挑着一担一百来斤的小麦去田芯村磨粉。后来因为修建里石门水库,田芯村的人绝大部分都移民走了,碾米机器间应该早就埋在水库底了。一次聊起此事,妈妈还笑呵呵说:“那白粉做成的包子,手不干净的人一按一个印。”
在小溪边,小麦粉的主要用途是做手擀面和面皮。手擀面,可以用二遍粉黑一点的切。姐姐揉的手擀面总是不够硬,常叫我帮忙,说我的手劲好;而面皮,必须用头遍的白粉,最后要拉长,差的粉一拉就断。水平高的磨粉师傅,头遍磨出的白粉会更多一些,这也是妈妈每年要到离家三十多里的田芯村去磨过年粉的原因。
每年正月初二,隔壁邻居三家人会聚在一起做过年的豇豆包子、洋糕等,三家的灶台上都码着一人多高的蒸笼。妈妈置办了一整套品质上乘的蒸笼,蒸的时候,一点都不漏气。蒸出的包子、洋糕,白白的,漂漂亮亮。而且,用糕水做成的包子会越蒸越白。那洋糕,妈妈会拿出一部分切成片,烘干,就成了过年时最受小孩们喜欢的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