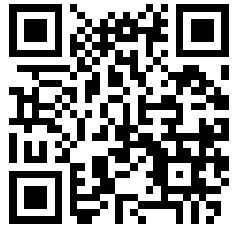“于欢”案的二审审理无疑是近年来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公开、透明的审理方式,让公众充分感受到司法的严谨、公开、公正,从而有力增强了法治信仰、树立了司法权威,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让公众充分参与对案件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正当防卫这一关涉公民基本权利行使法律条款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效提升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守法意识,这在大力倡导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今天尤为重要,切实体现了司法注重指引、规范人民生活的重要功能价值。
对正当防卫的理解与适用,理论和实务界在不法侵害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可以防卫的不法侵害范围、正当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等问题上尚存在一定的争议,“于欢”案二审裁判文书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从防卫的目的、时机、对象、限度等方面对于欢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论证,既紧扣法律条文规定,又充分吸取了学术界关于正当防卫的有益观点,同时,充分考虑了天理、人情等伦理道德因素,切实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裁判遵循“国法”、不违“天理”、合乎“人情”的要求,对类案的审理将起到重要指引作用。这里,笔者仅从学理角度,对裁判文书中的一些观点作简单述评。
一、如何把握正当防卫条款的立法精神。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第20条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三处重要修正,其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就是为了强化防卫权,鼓励公民勇于实施正当防卫。应当看到,刑法对正当防卫、见义勇为行为的倡导、鼓励,不能简单理解为法律要求公民不考虑面临的危险程度和自身反击能力,一味选择防卫,所以刑法第20条也仅是授权性规定,而非强制性的规定。这种鼓励,应理解为,法律通过豁免或减轻防卫人的责任,为防卫权的行使提供必要的保障,从而为公民实施防卫行为扫除后顾之忧,使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斗争。按照这一立法精神要求,笔者认为,在司法程序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也应当贯彻总体从宽的政策要求,一方面要从宽掌握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和条件,应当认定的要积极加以认定,确保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得到正确评价;另一方面,对属于防卫过当的案件,在量刑上要切实体现从宽的政策要求,从而以司法兑现立法价值,为公民与不法行为相抗争提供有力的武器,促进全社会形成维护正义、弘扬正气、保护善良的良好风气。至于“于欢”案件,二审裁判文书正确把握了正当防卫条款在鼓励公民与犯罪行为作斗争方面的立法精神,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案件涉及的人情事理,体现了对正当防卫的条件和限度适当放宽,不仅认定了于欢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并且显著减轻了量刑,为正当防卫条款的司法适用树立了正确的导向。
二、如何判断正当防卫前提条件。我国刑法对作为正当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的范围规定较为宽泛,不仅包括侵害人身权利的不法侵害行为,还包括侵犯财产以及其他权利方面的不法侵害行为;不仅包含犯罪行为,还应包含违法行为,故不能将不法侵害片面理解为暴力不法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不法行为,如侵犯知识产权、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其不法行为通常不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紧迫性,且通过报案、控告、举报可以有效实现对相关权益的救济,如果将其纳入正当防卫的对象,不仅将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问题诉诸暴力,造成更大权益的受损,并且因相关行为性质界定中的争议,可能导致防卫错误。所以,基于正当防卫的“应急性”,应当对防卫对象作出必要的限制解释,也就是要判断不法行为是否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紧迫性,从而确定是否存在防卫必要。如,对非法拘禁行为,其因限制人身自由,具有侵害的紧迫性,可以成为防卫对象。对侮辱行为,如果仅限于言语辱骂,侵犯人格尊严程度较轻,且仅涉及精神层面的权利侵害,不应成为被防卫的对象;而对肢体侮辱,同时伴有非法拘禁、轻微殴打行为,同时侵害他人人格名誉权、人身自由权以及健康权等,当然可以成为防卫的对象。对多个交替、间隔或连续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应当从整体上评价防卫必要性,即便个别不法行为违法程度较轻,或间断停止,但全部不法侵害并未完全终止,且被害人仍面临不法行为继续侵害的危险时,应认定不法侵害仍然存在。我们看到,“于欢”案二审裁判文书坚持了以上观点,对司法实践认定正当防卫前提条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然,对认定不法侵害是否存在的标准,如,对不法侵害状态是否结束,是以被害人主观认识为标准,还是以客观上不法侵害是否现实存在为标准,这些问题,在学术界还有进一步研究、探讨的空间。
三、如何判定正当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理论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基本相适应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必须与不法侵害总体相适应;必需说认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应从防卫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衡量,应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实际需要作为防卫的必要限度。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可以综合考虑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不仅是指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而且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应当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基本相适应。判断必要限度,不可能脱离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根据具体案件中双方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就“于欢”案而言,于欢在其母子人身自由遭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加害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具,警察已到场后又离开但尚在附近的情况下,为制止不法侵害,摆脱困境,使用致命工具捅刺被害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二审裁判文书对此作出全面评判,一方面,结合防卫人面临的冲突烈度和环境情势,对防卫行为的手段、方式和强度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进行了评判;另一方面,对防卫行为所损害的法益与保护的法益种类、大小进行了权衡、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于欢的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这对司法实践在认定正当防卫限度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对防卫过当如何定罪量刑。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理论上一般认为主要是过失,也有间接故意。具体到本案,于欢在主观上应是间接故意的伤害,其中对不法侵害人杜志浩的反击行为属于伤害致死,因此全案定性为防卫过当下的故意伤害罪是正确的。对防卫过当构成犯罪的,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考虑到本案之过当行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对于欢不宜免除刑事处罚,而应当减轻处罚。至于减轻到什么幅度,由于考虑到于欢行为虽构成防卫过当,但系因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导致其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而处置过当造成的违法后果,所以对其所实施违法行为非难的程度应当降低,应显著减轻其责任。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于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笔者认为是适当的。这对今后司法实践处理类似案件,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